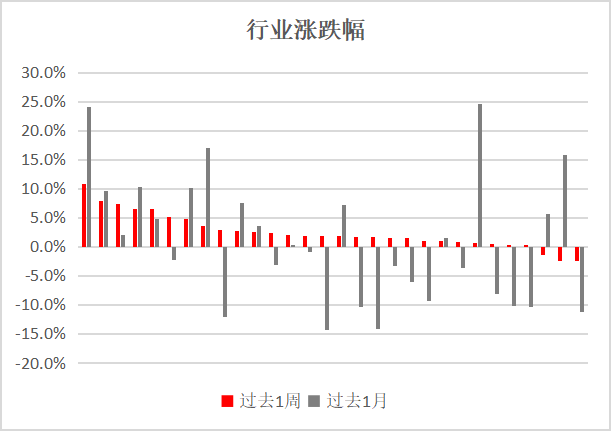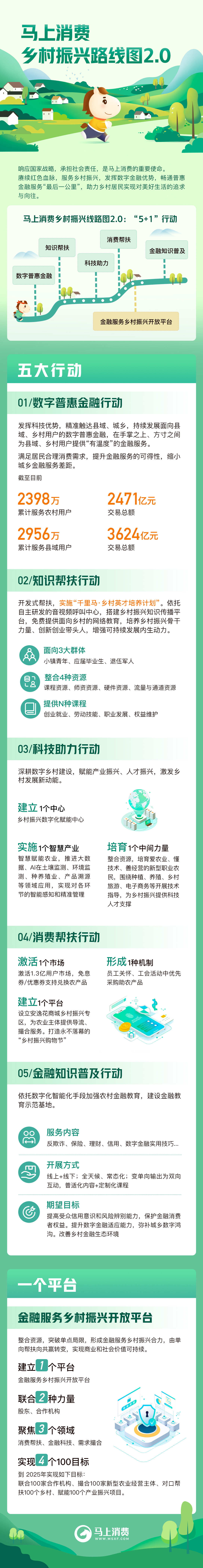PPP就是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社会资本
北极星节能环保网讯:近年来,PPP项目引起各界关注,环保领域PPP项目也在逐渐增多。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迅速升温的近两年时间里,各级政府、各部门、学术界和实务界对PPP的诠释不断拔高:PPP不只是减轻和转移财政压力的融资手段,更是为了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PPP可以增加、优化公共产品和服务,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PPP是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PPP重新定义国家公共治理……这些愿景未来都有可能借助PPP来实现,但在当下,PPP就是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如果连这个基本目标也不能达成,何以奢谈其他。
PPP实务中经常会发现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并没多大兴趣,除了规避利益输送之嫌外至少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来,中央没有把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口子堵严,明股实债、加长版BT、保底收益等变相违规举债项目仍然畅行无阻,也鲜见监督检查和严肃追责。二来,中央部委和各级政府投放了规模庞大的PPP杠杆资金——前补贴形式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联手能够轻易套现变成专项资金来用,引导资金成了先导资金;后补贴形式的,地方政府可以包装成“应收账款”来为举债增信。能够通过举债和上级补贴来大干快上时,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劳神费力去和社会资本慢慢谈合作。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只是措施,目的还是提供公共服务)缺口也大,这是客观现实,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的想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举债、中央部委引导基金等杠杆方式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则仍然无法解决控制政府债务和提高政府投资效率问题,与行政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道而驰,会让改革陷入悖论。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引入非公有资本——特别是民营企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但是,从现实情况看来民营企业对PPP的反应也冷淡。主要原因有,缺乏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经验、对PPP缺乏足够认识、缺乏低成本融资渠道、对地方政府信用缺乏信心。这些都与民营企业过去缺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会有关,面对“天然”的障碍,政府刺激往往会被谨慎的民营企业当成鱼钩上的诱饵,以加杠杆的方式引导民营企业是头疼医脚。也不排除有冒险型的民营企业会受杠杆资金诱惑贸然参与进来,但PPP合约期一般长达10至30年,专业性强,风险大,而且还不能给予暴利回报,非理性的社会资本会进入势必会导致项目失败,甚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阿基米德说给他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地球,没说要一根杠杆,因为支点是杠杆原理的基础,如果没有支点,杠杆作用无法形成。PPP的支点是全社会对PPP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支点,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也只能变成支柱,自己撑着,而不能真正形成杠杆效果;有了信心支点,资本会自然聚合,或立于支点之上支撑PPP,或横于支点之上撬动PPP。政府资源应该用于构筑全社会对PPP的信心支点,而非做杠杆,具体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其一,交学费。对于PPP,政府、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和咨询机构都没有经验,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民营企业更是相对滞后。当前推行的PPP体量都比较大,试错成本太高。为了避免长远、沉重的代价,短期内应该不要纠结于狭义的财务成本,要拿出一些资源来培养人才,培养信心,积累经验。包括对民营企业进行PPP培训;拿出一些几千万元的小项目来专供民营企业之间竞争,逐步培养民营企业的公共服务投资运营能力、提高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正规化PPP操作经验(政府和国有企业合作达不到这一点)等等。
这样做,短期内可能会导致“不物有所值”,但只要有充分的竞争,这就不算是对民营企业输送利益。即使当下小规模的项目用PPP模式会比政府自建自营多花一点钱,这是政府构筑信心支点引导民营企业投资公共服务领域的必要成本,也是为未来大型项目节省试错成本所交的“学费”,不能算小账。
其二,去库存。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多里,我国基础设施的匮乏模糊了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界线,改革、技术、人口、自然资源等红利也暂时掩盖了政府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受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政绩考核制度、地方与中央财政二次分配博弈(例如中央为取消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买单就让一些地方政府尝到了举债的“甜头”)等因素影响,全国各地纷纷运动式上项目,特别是工业区和开发区、生活配套基础设施,最终产生了大量低效投资和政府性债务。如果继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比赛,烂摊子和政府性债务必然会加剧。从全国范围来看,基础设施不是不足,而是不均衡,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的三四线城市就有大量的高标准过剩工业区和生活配套设施,向这些地区导入产业和人口可以盘活政府存量资产、消化政府存量债务。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存量债务,民营企业就敢参与PPP。
当然,由此也会产生“过去大拆大建和欠债多的地方现在占了大便宜”的争议,可由中央引导地方政府之间合作(Public-PublicPartnership),进行区域间产业置换和产业整合;也可以调整增值税的中央政府分成比例,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承担星碎产业和人口流出地区更多的事权,支持这些地区往农业、旅游、养老、互联网等对基础设施依赖度较弱、未来市场需求较大的方向发展。
其三,保民生。公共服务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公众的幸福感,感知在经济学中是效用问题。过往的二三十年里的基础设施大建设唤醒并撑大了公众需求,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把有限的政府资源用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年限、对社会保障扩大范围和提高基本线等,这些过往投入不足的社会保障服务领域更易于提高公众幸福感、提高社会稳定,并激发民间投资。社会资本是个大概念,不仅是民营企业财团和资本家,当低保、教育、医疗、养老、殡葬等后顾之忧由政府托底之后,各行各业的民间投资都会更积极,社会资本聚合机会更大,民营企业参与PPP的动力和实力自然会增加。
另外,社会保障以基本服务为主,而且多是非标准化服务,绩效考核难,引入民营企业投资条件不成熟,短期内也仍宜以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为主。举个例子,在民营医院的基本医疗费用可以社保报销,这也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但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上严重不对称,医疗又不是标准产品——同一种病,给每个人开的药品和药量都可能不同,导致患者处于弱势地位,“魏则西事件”暴露了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并不一定能提高效率,甚至有可能发苦难财。相比之下,房建、交通、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成熟度高、产出要求明确、市场竞争充分、资金需求量大,可以尽量交给民营企业做。
“交学费”解决了社会资本的问题、“去库存”解决了政府问题、“保民生”解决了公众的问题,政府资源用在这些方面才能构筑全社会参与PPP的信心支点。商鞅变法就是从“立信”开始,效果立杆见影。当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面临资产荒,只要政府的劲使对了,应该很快能达成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社会资本的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生产者和管理者,后来逐步朝两方面发展。据清华大学王守清教授的研究,公共服务的主体由政府统管往国有企业、公司法下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公共服务项目的交付方式由计工(件)制往分包、工程总承包、EPC(“交钥匙”)、融资+EPC、融资+EPC+运营(BOT)发展。两个方面殊途同归,都朝向一个方向——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PPP)。
公共服务主体和交付方式的发展明显提高了效率,政府越开放、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共服务越多越深的地区经济往往越发达。由此可见,PPP不是谁炮制出来的革命性工具,而是经济发展和公共治理的必然方向。做PPP也没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谁根正苗红的问题,更不应该有“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零和思维,还是要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用好公权和公款等资源,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优势互补、有机组合,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