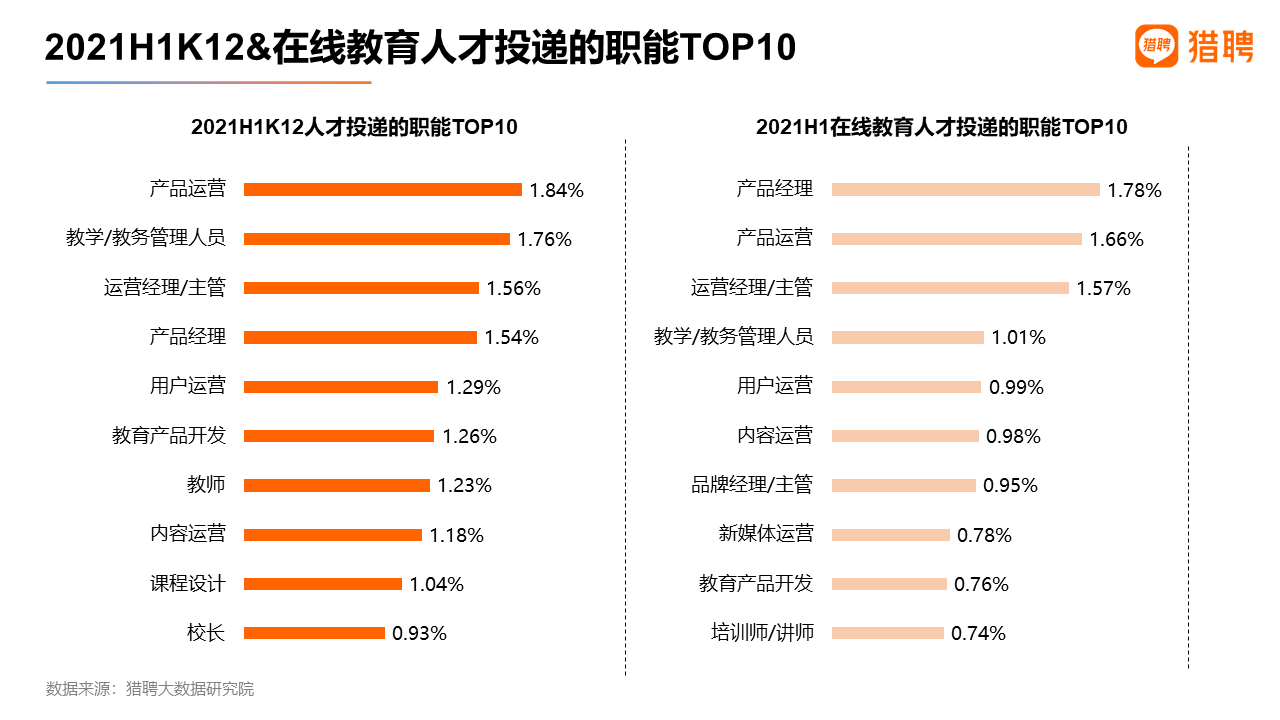真正的宇航员怎么看《星际穿越》这部电影?
此问题最初出现在问答网站Quora上:真正的宇航员怎么看《星际穿越》这部电影?
作答的是美国宇航局(NASA)前宇航员加雷特·赖斯曼(GarrettReisman)。
几天前,我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几个人找了个下午去看了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Nolan)的《星际穿越》(Interstellar)。我们都很喜欢。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很少出去,可能看部《鸳鸯绑匪》(Gigli)都会心满意足。
就个人而言,这部电影我从头到尾都很喜欢,但有几处有失精准的地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演员班底。出演每一部宇航员电影的都是马修·麦康纳(MatthewMcConaughey)、安妮·海瑟薇(AnneHathaway)、乔治·克鲁尼(GeorgeClooney)、桑德拉·布洛克(SandraBullock)、汤姆·汉克斯(TomHanks)和凯文·培根(KevinBacon)这样的演员,有必要吗?
这叫我情何以堪?我只有5英尺5英寸(约1.65米)好吗!
什么时候能请保罗·吉亚玛提(PaulGiamatti)或华莱士·肖恩(WallaceShawn)来主演一部太空动作冒险大片?一次就行!拜托!
有一些小差错值得一提(下文存在剧透)。
比如,像NASA这样庞大的一个政府机构,它召开的会议是不可能只有十来个人参与的。
其次,和其他很多描绘通过旋转航天器构造来实现人造重力的电影一样,坚忍号(Endurance)的直径还不足以营造出与地球相当、不至于令人晕眩的重力。
最后,如果一个先进文明可以创建一个时空书架的四维超正方体,那他们为何不给它装个白板?
我知道,掉落的书籍、表现异常的手表和表现出二进制图案的灰尘都是更加戏剧化的沟通手段,但若要解释一种全新而具有一致性的重力理论,用公式和图表还是要比一组看似随机的二进制数据来得简单得多。
但《星际穿越》中有很多刻画对了的地方。很多相对论效应表现得恰如其分(至少我一些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老同学是这么跟我说的)。
在电影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太空硬件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用于保存人类后代冷冻胚胎的冰柜看上去跟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SpaceStation)里那个一模一样(里面装的虽不是可以让人类布满一个星球的遗传物质,但这也许是个好主意……)坚忍号半球形的窗户也跟国际空间站穹顶舱(Cupola)如出一辙。
而Endurance上很多开关面板也有模有样。而我们也都知道,爱真的能超越时空。
我尤其想提一下库珀(Cooper)手动操控飞船的频繁程度。似乎他每5分钟就要抓起手柄手动控制一下,这跟现实世界趋势大相径庭。
作为一种隐喻,这显然代表人物为控制自身以及人类命运的奋力挣扎。
《星际穿越》表现了美国人对自由意志的强烈信仰——认为我们都是能够做出选择并塑造自身命运的自由个体。
然而,与这种自由选择权形影不离的,是责任的重担,比如布兰德教授(ProfessorBrand)就徒劳地想要以他所期待的方式左右人类命运,最终这个愿望还是化为泡影。
但自由意志是典型的美国英雄原型——那个探索者、先锋,那个凭借技能、决心和主动性挺身而出、拯救世界的人,也就是电影中的库珀。
其他文化可能将集体努力视为价值所在,抑或是相信命运,而不是歌颂个人成就,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人欣然接受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重担和回馈。
这种原型与美国的国民性密不可分,而且很有必要坚守这种神话故事来激励下一代库珀们,在人类面临太空新的疆界时挺身而出。
当然,《星际穿越》的主题还是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电影的这个层面绝对引起了我的共鸣。
不久前,我参加完一个演讲活动,穿着我蓝色的NASA宇航员飞行夹克回到家,把四岁的儿子送上床上安顿好。他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又刚去过太空。
我告诉他没有,他问,“那你很快又要去太空了吗?”
“离开你,我是不会去的。”我诚恳地回答。
放心和满意的表情掠过他的脸颊,但很快就被担心所取代,他皱起眉头:
“可是我没有飞行夹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