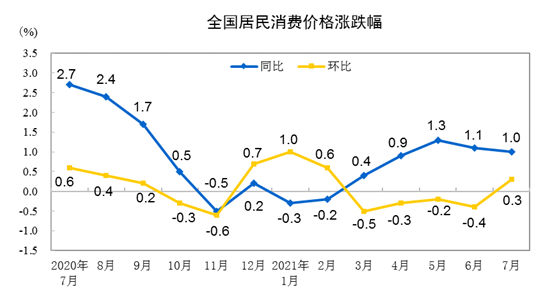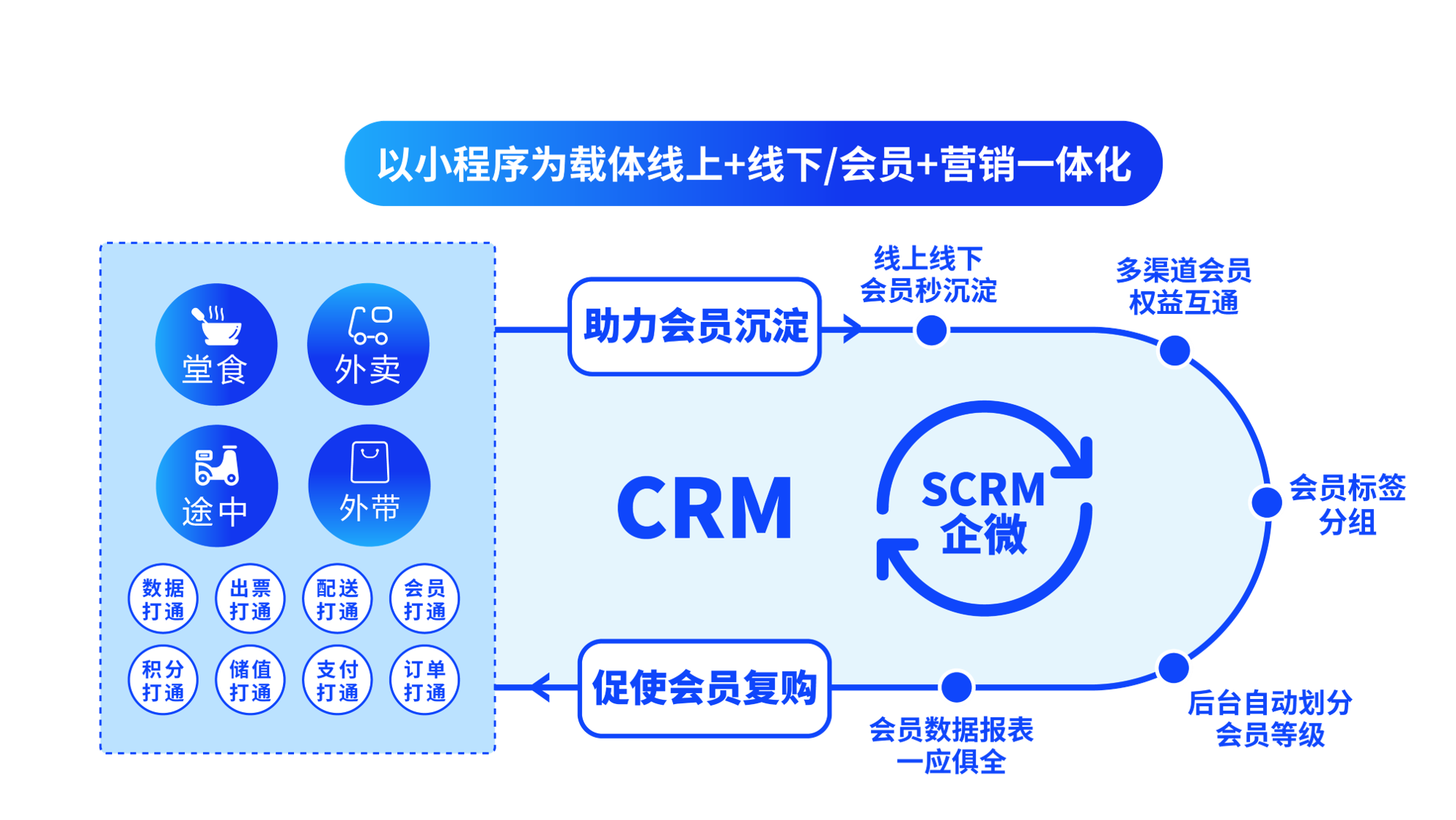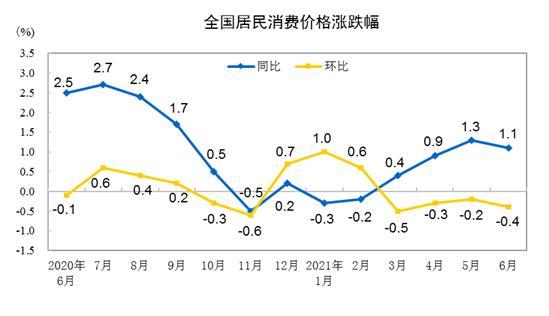现代人对智能化又爱又怕
在智能时代,我们是否想过,那些科技产品是我们呼来换取的工具,还是我们已经变成它们的俘虏?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的效率越来越高,但交出去的隐私也越来越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吗?我们自身和科技的关系会保持平衡永久稳固,还是突然有一天打破平衡,上帝重新选择一个主宰者?这篇文章会告诉你答案,非常值得一读。
如今媒体上的科技新闻读起来令人感到害怕,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NSA监听的最新证据;新设备和App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以及最新的个人信息泄漏案等,这些严重威胁着个人隐私。其影响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对作为自由思想基石的私人与公众分割的快速侵蚀,并将对我们的自由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或许会为此感到沮丧,然而实际上我们却也漠不关心。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曾经参与或发起过抗议(智能设备对隐私的侵犯)?或者哪怕是改变一下我们跟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表的关系呢?为什么我们会对此如此漠视呢?
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习惯问题,我们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使用这些设备而无法想象到有任何别的替代方式。或者说,我们可能开启了悲剧的命运,由于我们对于这些科技公司的无能为力,我们除了接受隐私受到侵蚀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这些都是未触及本质的事后解释。要触及核心,我们就必须深挖文化底层以揭开那些塑造我们与科技之间关系的理念。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出现一次意义深远的思想转变。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我们对这种关系一直有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们把科技看作是对人的解放,甚至被DavidNye(历史学家大卫?奈伊)、JamesCarey(传播学教授詹姆斯?凯瑞)和其他学者推到了神圣的位置。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它视作非人性化的、使人异化的、甚至是有可能操纵人的,这种观点的历史代表人物是WilliamBlake(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MarkTwain(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yShelley(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CharlieChaplin(英国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FriedrichNietzsche(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NedLud(勒德运动领导人奈德?勒德)、SmuelBeckett(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和KarlMarx(德国政治哲学家及社会理论家卡尔?马克思)等,然而这一派观点在过去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已经被人们所抛诸脑后了。
许多文化领域见证了这一转变,但没有一个领域像科幻电影这样直白。即使以未来为设定,科幻将目前关于技术的看法探索式的搬上荧幕。而事实上,很多优秀科幻电影的成功无疑是因为它们清晰的表达了那个时代对技术的希望和恐惧。
20世纪后期的科幻电影清楚的表明了陈腐的对技术忧心忡忡的观点在美国文化中的流行。例如,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个人电脑的出现、基因工程和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工业机械化带来的失业,以及新潮的军事技术如战略防御倡议(又名“星球大战”计划)。
当时的科幻电影流露出一种恐惧文化,生怕我们跟不技术上变化的步伐。许多科幻电影探索了技术的去人类化效应,描绘了人类失控的世界。像《终结者》就结合了对机械化和计算机操作的担忧。人类主人公无法直接杀死施瓦辛格扮演的赛博格(半机械人),后者最终在与另一项工业科技(一台液压机)的较量中走向毁灭。同时代的又一经典力作《银翼杀手》描述了一项复杂的思想实验,将技术和人类组合成“混血儿”(hybrid混合体)。哈里森?福特饰演的戴克必须歼灭的对手--罗伊,象征着不受约束的人类野心和技术潜能的可怕合成。20世纪90年代是大规模计算和互联网兴起的时代。相应的,新的技术隐喻被创造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阳刚技术被流变的网络所取代。在《终结者2》中,施瓦辛格的工业杀人机器已经过时,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取而代之的是来自T-1000的威胁,T-1000的速度和液体金属形态唤起了一个全新的由数据流统治的世界。
90年代也见证了日常生活的日益数字化和虚拟化--这一趋势反映在JeanBaudrillard(法国哲学家)的观点中,他认为海湾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虚拟化战争。电影也在探索着生活虚拟化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楚门的世界》、《黑客帝国》这两部电影都讲述了主人公被从日常生活“唤醒”后,发现所谓的日常生活不过是人为创造的产物。
然而,科技恐惧观点很少出现在2000年以后的科幻电影中,同时,我们也很难搞清这些电影的共同主题或者属于那种电影类型。难道正如《异形》和《银翼杀手》导演RildleyScott宣称的那样,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特定的电影题材已经江郎才尽?还是这预示着文化中的某些深层次问题?
最近有两部电影确实表达出了对科技的恐惧,在对它们进行反思后答案也就清楚了。《超验骇客》和《Her》是众多讲述人工智能失控电影中的两部。然而,它们都没能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仅仅因为它们是“坏电影”(译者注:恐怖片、科幻片、怪物片等都被称为badfilms)?不一定。尽管《超验骇客》很难让人接受,但是,《Her》的主题却耳熟能详,对数字虚拟时代的爱情进行了深入探索。但症结在于,两部电影都没把握住时代精神--没人真的再对人工智能心存恐惧了。
对科技心生畏惧的观念,离不开三个前提:首先,科技和人类相互分离,自给自足,这符合古老的人类机器二分法。其次,科技具有自己的特性--它能主宰人类生活,传奇的传播学家MarshallMcLuhan曾说过,我们被自己制造的工具重塑着。第三,自然能够指挥科技与人类为敌。
然而,近20年这三种假设发生急剧坍塌。尤其是我们不再认为科技有内在涵义,媒介也不再是信息(McLuhan说过媒介即信息)。相反,科技唯一的价值是我们所给予的。对我们而言,科技是一张白纸,等着我们赋予它文化内涵。随之相关的是,我们对自身与科技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与科技之间的界限正在土崩瓦解。
或许核心的驱动因素在于,以科技为中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诉求。我们需要证明自身的独一无二性,而科技已经成为达成这项目标的最有效途径。我们把科技视作自我表达的途径,它使我们更好的展现自我。
智能手机就是很好的例子,黑莓最第一次为智能手机赋予了文化内涵,它的定位就是商务工具。这影响深远,如今各大智能手机品牌都把他们的产品定位成社交关系、创意性表达、玩乐及所有其它有关彰显独特个性的中心。App同样重要:它们通过提供定制化体验来使得智能手机充分表达出用户的个人诉求。
有助于用户进行自我表达的理想技术并不仅限于智能手机,但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者不再以创造出拥有终极智能的机器为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计划复制人类真正的特质,如作曲和绘画等。
直到最近,在苹果智能手表的发布会上,JonathanIve表示,“我们处在激动人心的开始,我们正在设计的技术能够可穿戴、真正个性化”,这预示着一场新的旨在消除人们与科技边界的战斗已经打响。
与之相似的,物联网让我们前所未有的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在这里,我们在感觉到症状之前就能提前知道病情;在冰箱的牛奶喝完之前就能及时收到通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技术,它与我们的需求如此合拍,以至于在我们的需求产生前它就能进行提前预测了。
因此,我们现在没有只把科技看作是一种赋权,更是将其当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因为它的作用就像是一把能够打开我们心灵密室的钥匙,我们与之建立了新的亲密关系,这听起来像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看起来科技正在接近自身边界:这对人类的自由来说不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一种驱动力。
毫无疑问,这个乌托邦式的世界令人万分愉悦,但这丝毫不会削减意识形态的纯粹性。事实上,是科技的外表使得这种新的“亲密的意识形态”变得如此有魅力。
在过去,由于人类机器二分法很容易把机器与人分开,所以我们能轻易的保留对科技的批评权。就这样,我们可以把机器看作是一个客体来分析;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发明如何使我们的自由变好或者变坏。但现在这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因为我们自身和科技已经融合在了一起。我们需要拼命与科技拉开一定距离,从而重新获得对科技进行思考甚至批评的能力。
结局可能是我们无法看见科技的阴暗面--它有可能被滥用,比如说用来侵犯我们的隐私。当我们把智能手机看作是第一个帮助我们发现自我的工具;当我们认为谷歌自动驾驶汽车是如此可爱;或者当我们相信GoogleGlass能够使我们找到一种超脱于身体的、掌控世界的方式时,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这些设备对我们隐私的影响?
这不仅仅在于我们对此的无视,更是在于我们深层次的意愿。“科技是自我延伸”这个观点的盛行催生了一些自恋情节:我们喜欢技术是因为我们喜欢自己。在弗洛伊德学说看来,亲密的意识形态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把科技当成寻求理想自我的核心要素,从而将自己的爱意投射到技术客体上。因此,我们不需要真正把自我和科技割裂开来,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外部的东西,并与内心的自我产生疏远。可能这就是亲密的意识形态能够操纵我们的真实力量所在。
但我们需要回到上一步,将我们自己从周围那些诱人的智能设备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结束对科技的盲目崇拜,重新和科技拉开到一个我们能够对其时刻保持“批评”状态的距离。我们可以试着这样看待技术:它们引领我们走向自由,同时也成为我们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仍未觉醒,等到那个技术乌托邦因为对我们隐私的重大影响而变成一杯毒酒时,就一切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