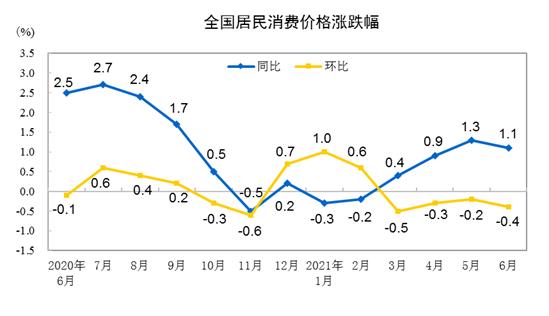进口药价格真正下降还取决于流通等诸多环节
国产影片《我不是药神》还未正式上映,就引发了一场全民讨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部关照现实的影片总是能够牵动我们对生存与命运的共鸣。更何况这样的影片又是如此稀缺。
影片的主人公程勇,本来是卖印度神油保健品的。机缘巧合,他为了“帮”慢粒白血病人,从印度带回了天价药(片中叫格列宁)的仿制药并私自贩卖,引起了警方调查……
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原型陆勇在罹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后,吃了两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花了56.4万元。不堪重负的他改用印度仿制药,这种药的价格只是瑞士药的1/20。陆勇后来将印度仿制药又推荐给了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被警方发现。陆勇的故事在当年轰动一时,有1002名患者在联名信上为他签字声援。最终,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我不是药神》旧事重提,再次将“看病贵”、“仿制药”这些话题引入了人们的视野——命悬一线的病患、被视为“药神”的带药者、坚决维权的制药公司、铁腕打击“假药”的公安,至此陷入尖锐而又复杂的冲撞与纠葛中,不断叩问屏幕前的每一个人: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做?
2015年,在陆勇事件之后,《经济观察报》曾经刊发题为《寻药》的封面报道,反映国内丙肝病人买不到、买不起欧美国家新药的困境。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也是辗转到印度买药——吃仿制药一个疗程只需900美元,相当于在美国治疗成本的1%,而中国当时采用的干扰素疗法成本大约在7万-8万元人民币。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轰动。
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病种、不同的寻药故事,背后的问题却是相似的。比如,有关生命权与专利权的问题。一方面,世界上存在着大量吃不起药的穷人。以格列卫为例,在陆勇吃药的时候,一个月的服用费用是23500元,尽管诺华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但是一年7.2万的费用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另一方面,研发新药的成本惊人。过去研发一个新药平均花费10亿美元左右,实际上新药研发的开支远不止这些。比如,世界著名药企阿斯利康在1997至2011年研发花费大概在580亿美元,期间只批准了5个新药,平均每个新药花费高达118亿美元——不消说,这里面包含了数之不尽的试错与失败的成本。
如果创新者不能享有其成果,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没有实验室、没有工厂再研制新药。还是那句话,没有专利药的创新,哪来仿制药的拯救生死?简单地将道义的责任压在制药公司身上,将冲突引向制药公司与病患之间并不公道,也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同样,我们也无法指望一个或者若干“药神”普惠众生。
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难题,但却绝非无解。这需要各方的努力,特别是政府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比方说,政府可以出面与医药公司谈判。这些年,巴西、马拉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有类似的案例。事实上,中国也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允许政府出于保护“公共健康的目的”,在专利保护期内授权中国药企使用国外厂商的专利技术,生产相关仿制药,但《专利法》颁布至今,中国还未曾动用过这一规则。
应当看到,从《我不是药神》故事发生的年代至今,中国相关政策的调整一直在持续。比如,格列卫等药品已经被纳入医保目录,报销比例最高80%左右。最近进口抗癌药关税的调降,也有利于减轻治疗压力——我们相信会有更多“救命药”关税进一步下降,但进口药价格真正下降还取决于流通等诸多环节。再如,新药进入中国通常要晚5-7年,这也是境外带药的动因之一。好消息是,中国药监局承诺加快境外上市新药审评审批有关工作,并宣布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
新政逐步落地可期,但也仍需要时间。对于很多病患来说,“药神”故事仍是现实存在。不过,面对《我不是药神》这道选择题,今日的我们应该有比过去更多的智慧和担当,也有更多的资源和条件。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还有多少像格列卫这样的救命药徘徊在医保之外?还有多少人行走在为吃药而自救的路上呢?这或许是电影之外,留给我们的沉重而迫切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