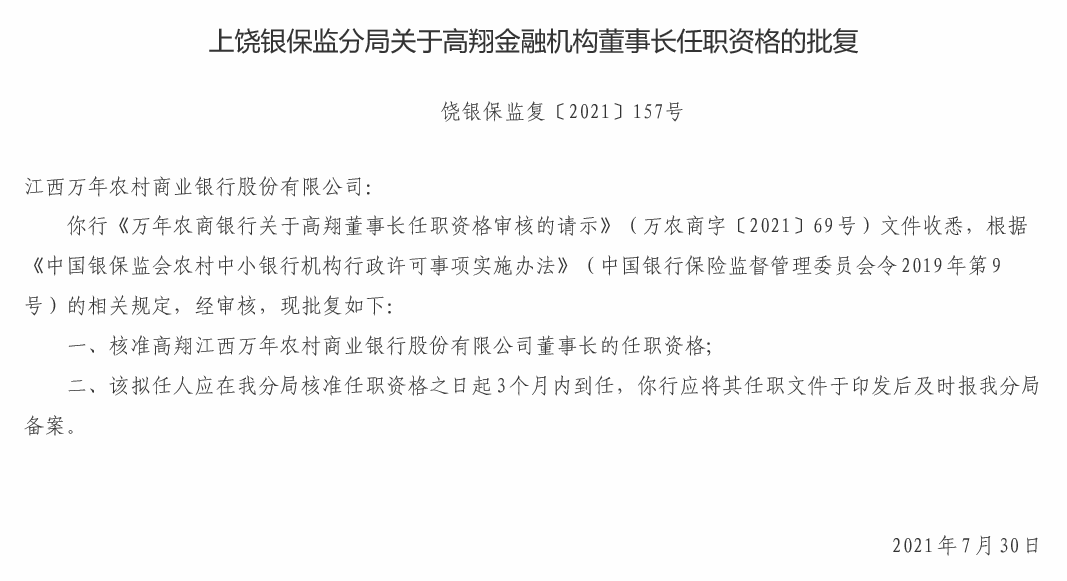如何寻求新型全球化发展?
如何寻求新型全球化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新平庸”状态。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产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原有的以“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大循环变得愈发不可持续。因此,如何从促进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与合作的角度来寻求新型全球化发展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战略命题。
本质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是世界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三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成为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的突出表现,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本世纪以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红利。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各国经济发展愈发依赖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升级。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本身不能保证一国能够获益,更无法确保一国自然地向全球价值链更有利位置攀升,甚至可能落入低附加值活动的陷阱。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正处于新的调整时期。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核心在于提高产品/产业的国内增值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取决于其专业化深度,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贸易量上,更体现在对全球价值的创造与获取程度上,一国产业升级也变得错综复杂,我们不能再局限于一个国家边界内研究产业升级,而要放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去研判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与贸易利益分配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APEC等纷纷致力于建立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全球价值链政策的研究制定,旨在改善全球价值链效率,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私人部门的公私合作,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进而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价值链革命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全球价值链和贸易深入融合的结果之一是在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的贸易份额超过最终产品的贸易份额。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产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演变,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分工网络体系,继续沿用传统贸易统计进行贸易问题的分析以及决策将不可避免导致对现实的误读和歪曲。
另一方面,在全球生产网络与增加值贸易发展的背景下,一国产业升级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不能再局限于一个国家边界内研究产业升级,而要放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去研判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与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特别是当前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化”“数字化”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形态,改变了原有贸易利益的内涵,亟须新的贸易统计方法和框架,即以增加值贸易统计来支撑相关的分析与决策。
基于这样新型全球化的背景,我们必须着眼于未来,面向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治理新框架来促进全球贸易的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为世界各国开辟了促进增长、提高竞争力和创造就业的前景,是理解“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而全新视角。然而,近几年来,出现了具有排他性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分离主义在内的“逆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的浪潮不仅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合作,更导致全球贸易增长遇阻。然而,全球化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全球化随着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以新一轮技术革命、数字革命为代表的产业重组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正为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积聚新的力量和新的发展动能。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包括亚太区域在内的全球经贸格局正在步入框架重构的阶段。摩擦、冲突、碰撞将会前所未有,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但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