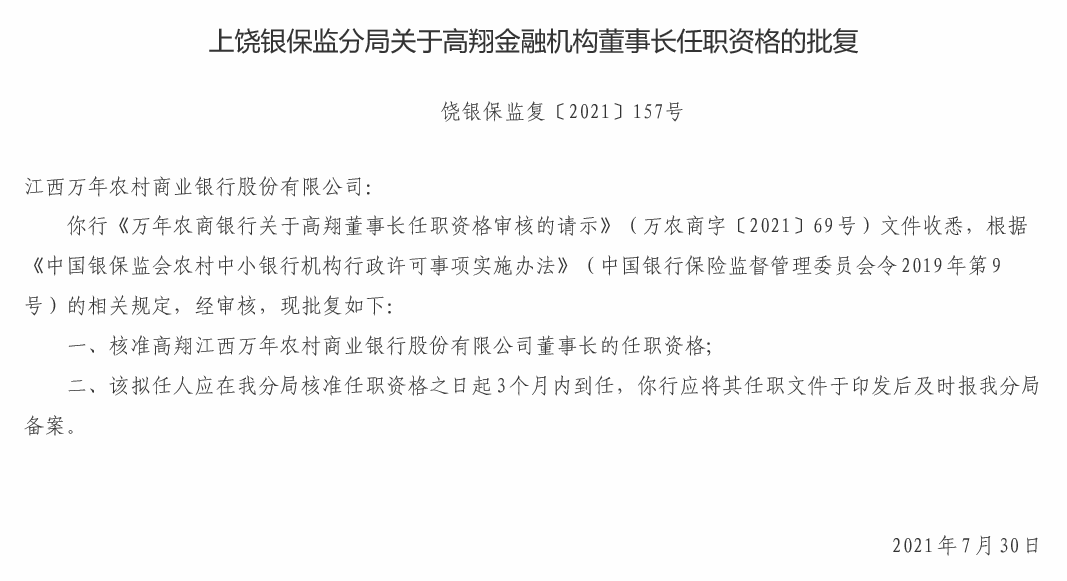火车、文学与政治
火车、文学与政治
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绿皮火车却转头开进了历史。
2014年6月29日中午12时30分,一列绿皮火车缓缓开出郑州火车站,出河南,经安徽,最终抵达浙江温州,全程24小时06分。“这是郑州铁路局的最后一趟绿皮车,也是跨局运行的最后一趟绿皮车。”郑州铁路局的绿皮火车时代,就此终结。
自打动车与高铁时代驾临以来,便不时传来绿皮火车退役的消息。有些地方甚至宣言,要“全面告别绿皮火车时代”。在这个速度、效率至上的国家,绿皮火车俨然沦为了缓慢、陈旧、落后的象征;而且,比起红皮车、蓝皮车、白皮车,它还是草根的象征,其票价相对便宜,“是农民工、低收入者出行的首选”。草根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些阔人眼中,它简直就是中国之恶的集中营。
因此,绿皮火车几乎代表了中国火车最低级、混乱、残酷的一面。有人说过,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中国,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去一个城市的火车站,乘一趟绿皮火车,当然,最好能赶上每年一度的春运。
我曾在《少年游》中写道:“绿皮火车的行旅,是我今生最不愿触及的记忆……大学四年,我乘火车,奔驰逾万里,亲历与见闻种种,彻底击碎了我对苦难的抒情。有一回从汉口到重庆,我只买到站票,竟一路站到安康,将近20小时,其间,我屡屡生出一种想法,不把自己当人,而视作货物,随地一扔了事,然而我终究没有勇气,放弃人之为人的脆弱尊严。”
这方面,最精辟的总结,莫过于王晓渔兄的那句名言:火车是文学的敌人。17岁之前,他对火车充满了浪漫而温情的想象,“对于一个‘庸俗浪漫主义’的少年来说,火车意味着传奇、景观和邂逅相遇”,“我为自己无法拥有一个冬天的旅行而伤感”。然而,体验过一次春运之后,“不仅使得我放弃了关于火车的文学想象,也逐渐使得我对自己从事的文学专业有些不满”。现实击溃了想象,火车碾碎了文学。
王晓渔曾提及一个情节,我们都不会陌生:一个文艺范的年轻人,背负行囊,行走于铁轨之上,铁轨漫长,通向无边际的远方。这样的镜头,不止出现在少年王晓渔所看到的流行歌曲的MTV里,几乎遍布与青春、爱情相关的影视剧中。我们不妨可以视之为一个隐喻,它蕴藏了文学对火车的浪漫主义想象。在文学青年看来,火车和铁轨,不是用来运输旅客,而是用来承载青春、诗歌、爱情与梦想,以及死亡。这是由文学建构的隐喻,隐喻反过来唤醒了文学爱好者虚妄的激情。王晓渔回忆:“这个现在看来不免可笑的镜头,却使得从未离开家门的我热血沸腾,执意在高考志愿上填满外省的学校。”
我与王晓渔都来自那个著名的民工集散地,都饱受春运与绿皮火车之苦。我们的区别在于,火车迅速粉碎了他的文学梦,我却依然在玫瑰色的梦中执迷不悟。我就读的大学,西门外有一条形同废弃的铁路,那四年的黄昏与黑夜之间,我曾无数次漫步于此,有时偕三五好友,有时则孑然一身,有时谈论文学、哲学与法学,有时什么都不谈,在缄默之中见证夜色降临,覆盖了我们的肉身、青春与时代……彼时彼刻,我沉浸于顾影自怜的抒情之中,似乎忘记了前不久所经历的绿皮火车的种种磨难。
我脚下的铁轨与绿皮火车驶过的铁轨并无本质的差异,却就此隔开了两个中国:一个文学的中国,一个现实的中国;一个抒情的中国,一个惨淡的中国。为了追寻前一个中国,我们往往遗忘后一个中国。须知这两个中国一旦距离太远,对任何一方都将构成巨大的伤害。
这不是要说,火车不能纳入文学的视野,不能作为抒情的道具。只是我们需要谨记,文学的火车不可与现实的火车背道而驰,对火车的抒情与想象,不可用来掩饰绿皮火车的苦难世相,譬如用“温暖而甜蜜的行旅”涂抹寒冷的春运。浪漫主义从不是一种原罪,然而一旦当其形成了对现实的遮蔽,则必须迎来批判。
对此,也许有人会用想象力为文学的火车辩护。事实上,我们生存的时代,最不缺的便是想象力,现实已经足够奇幻,如国人自杀的方式,挤爆了我们的头脑,超越了劳伦斯·布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即对现实的见证与记录,钱云会父亲的一曲哀歌,远胜于余秋雨、王兆山的无数赞歌;绿皮火车之上的一张春运图,刺破了飘在天穹的中国梦。
就此而论,绿皮火车不仅是文学的敌人,还可能是政治的敌人,对火车的浪漫化是文学病,对火车的美化,如对速度的迷恋,则是政治病。政治学上有一个流派,名曰“政治浪漫派”,它与文学青年同病相怜:不顾现实。中国高铁建设的高歌猛进,是否陷入了政治浪漫派的困境呢?空荡的高铁绝尘而去,将民众远远抛在身后,并遗留了重重难题。这被童大焕先生视为“一个时代隐喻”,他因此高呼:“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如今,绿皮火车渐次开往记忆,沦为古董,那一身锈迹,恰似历史的血痕。然而,无论高铁时代如何奔腾(我不反对高铁,却必须承认,高铁有高铁的问题,正如绿皮火车有绿皮火车的问题),铁道部如何重组,都不足以根本改善春运帝国的现状。痼疾依旧,动车与高铁的高昂票价,则成漂泊在外的农民工的新病。从这个意义上讲,火车依然是文学与政治的敌人,王辛笛的诗依然响彻在耳:“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